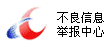因为有燕园而真实——只有这样一片响彻过中国最激进最昂扬的声音的土地才能更好的容纳新一代青年的慷慨之音。我是多么渴望在未名湖畔将《少年中国说》读下去、将《我有一个梦想》读下去、将屈原陶潜李杜苏辛读下去、将中国千百年来的气象读下去!而这个梦的载体也越来越明显——走进北大。
走进北大,我的创作之路便告开始。我不是才子,但酷爱为文写诗,即使我经常因潦草的字迹受到冷遇,我仍相信一个人的文章到了最后——褪尽了文字的表象和虚张声势的词藻的最后——凭借的是心灵。所以我可以读到流泪、写到忘情,可萌绿,亦可枯黄,高中三年,数千字的文章大概也写了几十篇,均系遣怀之作,不曾公开。孔庆东先生的“歪诗”甚是有名,“曾经美味难为菜,除却西施不是人”尤让我对先生和北大倾倒,故我也常仿其口吻作诗。“风花随春尽,雪月逐水落。恩怨到头来,就是比能活。从容为人死,化成坟一垛。要想赖活着,做仰卧起坐。”这是我为减肥而作。“门开随意迎朔风,机票何比竹蜻蜓。飞至唐宋寻文炬,惊起一场南柯梦。”这是有感于机器猫而写。诸如此类,不再列举。平日里写作为表正式我常用文言文,高二时还曾以文言书信一封抵作假条以求班主任陈雪梅老师网开一面许假回家,并颇以为得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三味,其肆意妄为现在想来仍觉汗颜。毕其一生,我最大的奢求就是在同样的月夜中和中国最杰出的头脑一起望着未名湖沉思、与中国最尖锐的笔锋并肩战斗——为真理、为自由、为正义。而我的这个梦想依旧只有在这里才找到依托——走进北大。
走进北大,我的人生之路才真正开始。我十分渴望能够深入人民了解社会进而有利于国家——这当然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我立志于进入北大研习人文科学,而我的身份却是一个理科生,这不得不说有些矛盾。分文理时我就曾经犹豫过——既然自己爱好文学、好读历史,为什么不去学文呢?在我看来,文理科之间本无太多的界限,所有学科的学习都是为了让人的认识更接近事物的本质,并能够在自己的不断摸索和尝试中找到更加接近事物本质的规律而传之后人。只不过着眼点的不同导致了所谓有“天壤之别”的两门学科。我选择理科正是出于考虑到高中阶段学习理科对我而言比学习文科更有价值——自然科学能够用更简捷的方式将一个相对真实的世界呈现在我的面前,让我在直面真实中清醒而沉稳——我选择文理的依据不在于我的长处是什么,而在于我到底需要什么。而现在我非常佩服当时我的勇气——理科确实磨砺了我的心智、增进了我对世界的认知。我的人生需要更大限度的实现其价值,无论在什么岗位——从政、从商、科研或著述都胸怀家国天下,以季羡林先生研究吐火罗文的坚持、陈寅恪先生如剥春笋般考据的细谨、傅斯年先生的刚直不阿为模板终其一生,哪怕死时,我也希望吟着冯友兰先生的“岂止于米,相期以茶”离去——而他们都无一例外是北大人!可以想见,实现我梦想的唯一途径只有——走进北大。
于是我申请参加北大保送生、自主招生考试,虽然我没有十足的把握进入北京大学,也深恨没有一门名为“朗诵”的考试科目,但是,为了无悔无愧于我十几年的梦想,我希望专家组的老师能够理解并支持我的选择——为一个蠢男子蠢蠢的追寻、为一个然而未烬的青春、为一个属于北大的灵魂、也为一个追梦人对梦的坚贞。
现在是十二月一日零点,也许再过一个月我就会坐在考场中“冷汗如雨下,弃卷叫妈妈”,就算如此,这也是我因为尊重梦想而生的选择,也是我活到今天在空间上与北大最近的接触,我愿意燃尽自己微末的光亮去诠释孔庆东先生十七岁时写下的一行:“几时借得冲霄浪,虽死望峰亦从容。”
而十七岁的XX也立誓于此——
海棠香逝留西府,野径云飞话未名。
翠枕红霞京华梦,竹杖芒履雁门冰。
燕歌千载寒易水,寒江氤梦望荆卿。
万里征途望乡月,一簑烟雨任晦明。
燕园行,壮士行,王图霸业何日竟?
龙泉隐箧锋未减,但将重掌扫青冥。
自誓夜阑无愀色,独聆萧瑟燕园行。
我并非把这次考试比作荆轲刺秦王。我只是希望,凭自己的努力在这条希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路上斩出一条坦途直通燕京。现在我的梦想已经在我的汗水中趋于完整,希望诸位老师胡乱适之,大可不必严家炎尔,让这个梦变成真实。
此致
敬礼
学生:XX
****年十二月一日凌晨一点作于家中